脊柱侧凸VCR/PSO截骨矫形失败的返修术
近年来后路全脊椎截骨(posterior vertebral column resection, PVCR)术被广泛应用于严重脊柱侧后 凸畸形的矫正中,具有单次手术矫正率高的优点[1-7]。但是该术式的大出血、神经损伤、感染和内固定失败等为其公认的严重并发症[1-9]。既往关于该术式并发症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神经系统并发症,针对内固定棒断裂的研究目前尚未见报道。本文回顾性分析在我院行PVCR 术后内固定棒断裂患者的临床资料,旨在探讨PVCR 术后内固定棒断裂的危险因素及翻修策略,以降低后续PVCR 术后内固定棒断裂的发生率。
材料与方法
1、研究对象
2003 年06 月至2011 年06 月,在我院行一期PVCR 术后随访过程中发现内固定棒断裂患者共7 例 (基本资料见表1)。其中男4 例,女3 例。病因学分类:先天性脊柱侧后凸3 例,先天性脊柱后凸2 例, 成人脊柱侧后凸1 例,神经母细胞瘤术后脊柱侧后凸1 例。初次PVCR 手术时年龄12-39 岁,平均24.4 岁。初次PVCR 术前侧凸Cobb 角平均40.3°±28.0°(9°~81°);后凸Cobb 角平均75.4°±23.0°(42°~113°)。 2、初次手术方法
本组病例初次手术均在全麻下进行。骨膜下暴露范围为所需融合节段,选择顶椎为截骨区,切除截骨椎体的椎板,切除范围需超过截骨节段上下至少半个椎板,以防止截骨矫形后因脊髓皱褶引起的神经压迫症状。截骨时先在椎体凸侧椎弓根旁行骨膜下剥离以显露椎体前侧方及上下椎间盘,再行凸侧椎体截骨。凸侧给予临时棒固定后行凹侧截骨,以防止凹侧截骨时的局部异常活动,凹侧截骨方法与凸侧类似。在切除椎体的同时,一并切除截骨椎体上下椎间盘及软骨终板。截骨完成后再两侧交替放置逐渐改变预弯角度的固定棒并缓慢对截骨处进行加压闭合。完成后取椎体切除所得的松质骨及同种异体松质骨行后路植骨融合术,如截骨面闭合不全,可行间隙内植骨或植入钛网等椎间融合器。PVCR 手术全程均在体感诱发电位 (somatosensory evoked potential, SEP)及运动诱发电位(motor evoked potential,MEP)监测下完成。
3、术后随访及影像学评估
初次术后3 月、6 月、12 月、24 月、48 月给予定期随访。若随访过程中有外伤史则进行详细记录。 所有患者随访时拍摄全脊柱站立位片,测量指标包括:(1)冠状面侧凸畸形Cobb 角;(2)矢状面后凸 畸形Cobb 角。同时评估内固定系统在位与否及植骨融合情况等。对于发生内固定棒断裂的患者,记录断 棒时间、发生位置,分析断棒的原因并选择合适的翻修手术方案。翻修术后随访原则同初次手术。
结果
1、初次手术矫形效果
本组7 例患者中初次PVCR 手术切除椎体节段包括T12(2 例)、L1(4 例)、L2(1 例)。术后3个月随访时侧凸Cobb 角平均14.0°±9.7°(2°~29°),平均矫正率为59.6%(30%~88.2%);后凸Cobb角平均29.7°±15.1°(12°~49°),平均矫正率为62.1%(48.3%~80.0%)。其中残留后凸大于20°的患者有5 例,后凸Cobb 角平均36.8°±11.0°(23°~49°)。
1 例神经母细胞瘤术后脊柱侧后凸患者(病例2)在PVCR 术前即存在下肢不全性瘫痪、步态不稳, 术后神经功能无改善。1 例先天性胸腰椎侧后凸畸形患者(病例3)因初次矫形术中出现右下肢SEP 消失、 左下肢SEP 潜伏期延长超过30%现象,唤醒试验中双下肢活动障碍,遂即进行了去除凸侧内固定、扩大椎板减压,保留凹侧内固定。术后该患者无神经损害表现。另1 例先天性胸腰椎侧后凸畸形患者(病例5)初次手术中截骨椎体发生脱位,未置入钛网或其他椎间融合器。本组7 例患者初次手术围手术期均无硬脊膜撕裂、大血管损伤、术后感染等并发症发生。 365医学网 转载请注明
2、内固定棒断裂时间、位置及原因
7 例患者内固定棒断裂发现时间为术后6~53 月,平均23.4 月;其中5 例为术后2 年以内,时间6月~23 月,平均12.2 月;2 例在术后2 年之后,时间50 月~53 月,平均51.5 月。断棒水平包括T12(2 例)、L1(3 例)、L2(2 例),其中6 例(85.7%)与切除椎体水平一致,另一例患者(病例1)断棒发生于截骨椎体下一节段水平。断棒发生后随访侧凸Cobb 角平均19.0°(3°~38°),矫正率丢失平均为6.4%(-33.3%~44.4%);后凸Cobb 角平均41.6°(31°~51°),矫正率丢失平均为21.5%(1.1%~59.6%)。7 例患者内固定棒断裂的可能原因包括:(1)残留后凸(1 例,病例1);(2)残留后凸合并步态不稳(1 例,病例2);(3)残留后凸合并单棒内固定(1 例,病例3);(4)残留后凸合并后期钛网移位(1 例,病例4);(5)残留后凸合并前柱缺损(1 例,病例5);(6)外伤(2 例,病例6、7)。
3、翻修策略及效果
6 例患者于内固定棒断裂发现后立即进行翻修手术,另1 例患者(病例3)因拒绝翻修而选择佩戴保护性支具随访观察。翻修术式包括一期前后路联合翻修5 例,单纯后路翻修1 例。其中1 例患者(病例5)初次手术后前柱缺损明显,翻修手术时置入了钛网并行前路补充性植骨融合术;1 例患者(病例4)因钛网下沉明显,翻修手术中对钛网位置进行了调整(图1);其余一期前后路翻修患者均在后路翻修基础上进行了前路补充性自体植骨融合。6 例患者翻修手术均无神经功能损害、血管损伤、感染等并发症发生。翻修术后随访12~22 月,平均18 个月。末次随访时,侧凸Cobb 角平均14.8°±11.8°(4°~33°),平均
矫正率为56.6%(41.1%~76.4%);后凸Cobb 角平均23.2°±6.9°(10°~28°),平均矫正率为67.8% (53.3%~76.2%)。末次随访X 片证实植骨融合良好,未见内固定松动、断裂。
讨论
一、PVCR 术后内固定棒断裂的时间及位置分布
由于部分患者随访时间较短或失随访,PVCR 术后总体断棒发生率难以精确计算,且既往文献中尚未见PVCR 术后内固定棒断裂时间及位置分布的报道。Justin 等[10]发现,接受后路矫形内固定术的脊柱畸形患者,术后早期(≤12 个月)较远期(>12 个月)发生断棒的风险更大。他认为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是术后早期植骨融合尚未坚固,此时内固定系统的载荷稳定性较差,容易发生断棒现象。本研究结果表明,接受PVCR 手术的严重侧后凸畸形患者同样表现为术后早期断棒的风险较高。本组7 例断棒患者中,5 例(71.4%)发生在术后2 年以内,平均为术后12.2 月。这一结果提示,对于此类患者,在术后早期随访时就应警惕发生断棒的可能性。Justin 等的研究同时还发现,在18 例行经椎弓根椎体截骨术后发生断棒的患者中,16 例(89%)断棒发生在截骨水平或邻近截骨水平。本组7 例患者中,有6 例(85.7%)发生在截骨椎水平,1 例(14.3%)发生在截骨椎下一椎体水平。我们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截骨椎体水平往往是术后残留后凸的顶椎位置,同时可能存在前柱的支撑不足,在这一水平内固定棒所受的应力负荷相对其他位置更大,因而更容易发生断裂。
二 、PVCR 术后内固定棒断裂的原因
吕国华等[8]分析了2 例PVCR 术后发生假关节、内固定棒断裂的患者资料,认为植骨融合不良可能是造成PVCR 术后内固定失败的原因;本组7 例患者PVCR 术后随访X 片未见明显假关节形成,但翻修术中均见断棒处未形成坚固的骨性融合,这可能是因为X 片上局部存在大量内植物而掩盖了融合不良的迹象。邱勇等[11]认为PVCR 术后残留的后凸畸形显著增加了内固定棒断裂的风险。术后残留后凸增加了内固定棒的局部应力负荷,最终可导致断棒的发生。本组7 例患者中,除了2 例患者因不可控因素(外伤)导致内固定棒断裂之外,其余5 例患者初次手术后均存在较大残留后凸(>20°)。造成术后残留后凸的原因主要有:(1)人为残留后凸,避免脊髓皱缩损伤。本组1 例患者(病例5)初次手术中截骨椎体近、远端发生脱位,造成对位不良,导致椎间融合器置入困难。为避免脊髓损伤,最终放弃截骨间隙内融合器植入支撑,术后残留后凸23°。尽管该患者术后冠状面、矢状面平衡良好,但由于前柱缺损较大、内固定系统不稳定,最终于术后50 月发生双侧断棒。另1 例患者(病例3)初次手术时因截骨面闭合时脊髓监护信号异常,立即去除凸侧内固定、扩大椎板减压,保留凹侧内固定,术后残留后凸49°。该患者早期随访提示无明显失代偿,但单棒内固定稳定性不足,其本身就是内固定术后断棒的危险因素之一[12],最终该患者在术后4 年半随访时发现内固定棒断裂。(2)环形截骨不充分或脊柱侧后凸部分柔韧性较差,导致截 365医学网 转载请注明
骨间隙难以完全闭合造成残留后凸。本组其余3 例患者(病例1、2、4)虽进行了全脊椎截骨,但仍因环形截骨不充分或侧后凸部分脊柱柔韧性差等原因分别导致残留后凸畸形37°(病例1)、29°(病例2)、46°(病例4)。其中,病例2 因基础疾病术前即存在摇摆步态,术后步态无改善,加重了内固定棒的应力;而病例4 因钛网移位进一步加重了残留后凸畸形。
三、翻修手术策略的选择
既往研究证明,前路补充性植骨融合可有效提高前柱的支撑功能及内固定系统的稳定性,对重建矢状面上局部生物力学的稳定性具有重要意义[13,14]。邱勇等[11]认为PVCR 术后残留后凸畸形过大会导致矢状面上C7 垂线前倾,加上可能合并脊柱前方的椎体支撑缺损,会导致前柱支撑功能不足,单纯依靠后路内固定不能完全重建和维持脊柱矢状面的稳定性。而最符合生物力学原理的方法是后路手术的同时进行前路支撑融合。在本组6 例手术翻修的患者中,除病例1 因单侧棒断裂且初次手术后前柱高度恢复良好而选择一期后路翻修外,其余5 例均选择了一期前后路联合翻修,并根据患者具体断棒原因进行了个体化的术中处理,如置入钛网、调整钛网位置等。本组6 例患者翻修术后残留后凸矫正良好,末次随访时后凸平均23.2°±6.9°(10°~28°),未再发生内固定棒松动、断裂。由此可见前路补充性植骨融合在PVCR 术后断棒翻修手术中起重要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后路翻修手术时部分患者可不需重新置棒,而可在对位良好后使用多米诺连接器将断棒近、远端重新连接[15]。为了降低远期断棒的风险,对于初次手术后残留较多后凸畸形和明显前柱支撑缺陷的患者,可在初次手术后根据残留后凸的程度选择二期前路补充性植骨融合。
综上所述,PVCR 术后内固定棒断裂断棒多发生于术后2 年之内,断裂水平大多与切除椎体节段一致。残留后凸畸形是PVCR 术后断棒的重要危险因素,外伤、前柱缺损、摇摆步态、单棒内固定、钛网移位等增加了断棒的风险。正确选择个体化的翻修方案如一期前后路联合翻修手术可以获得较满意的疗效
声明:本网站部分内容来源于网络,仅代表网络观点,如有侵权请及时与我方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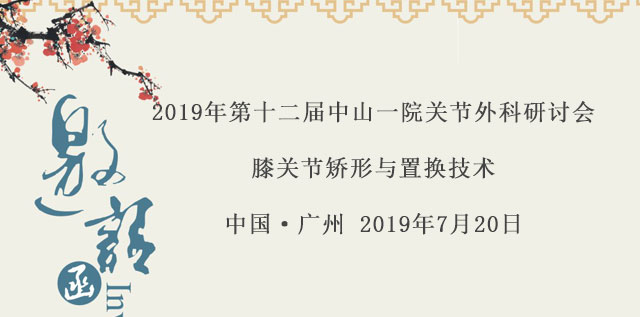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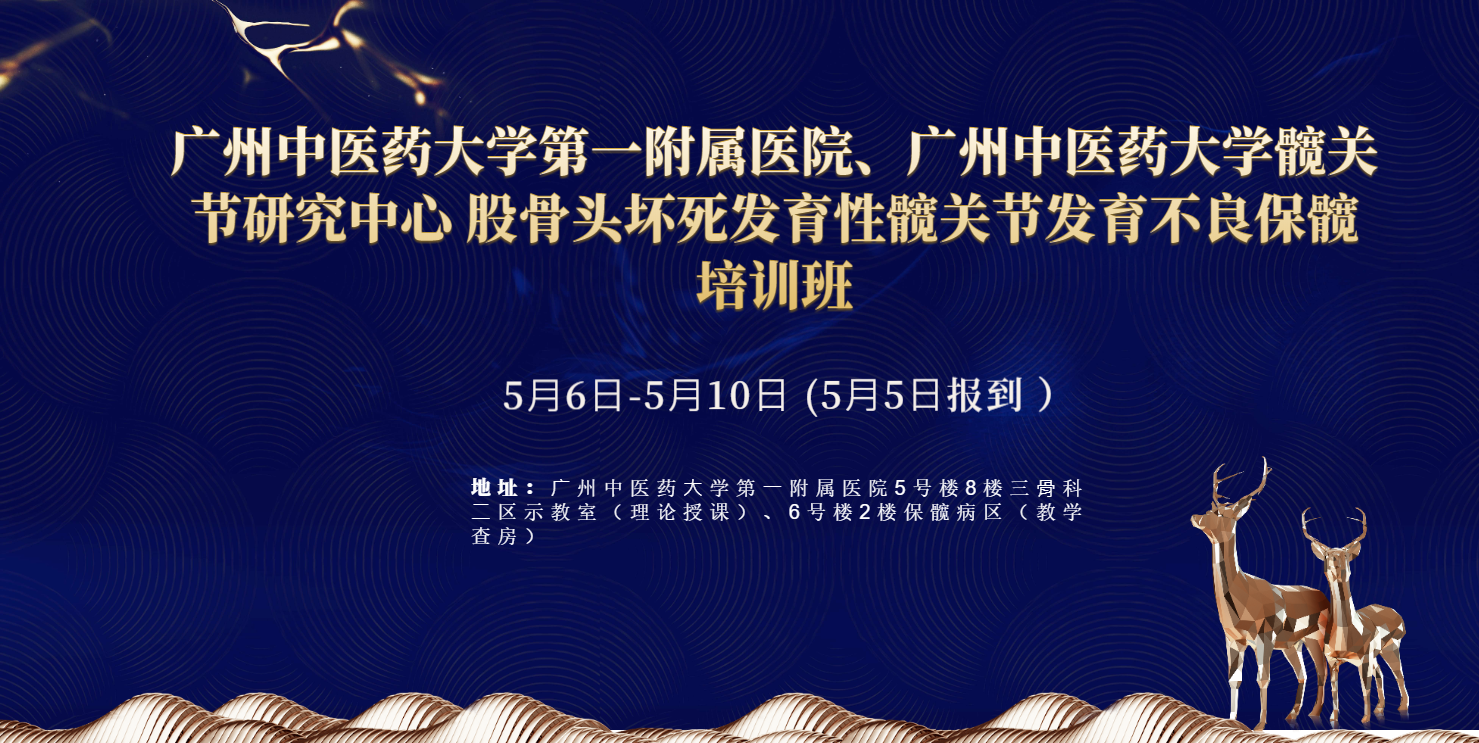

 扫一扫 关注玖玖骨科
扫一扫 关注玖玖骨科